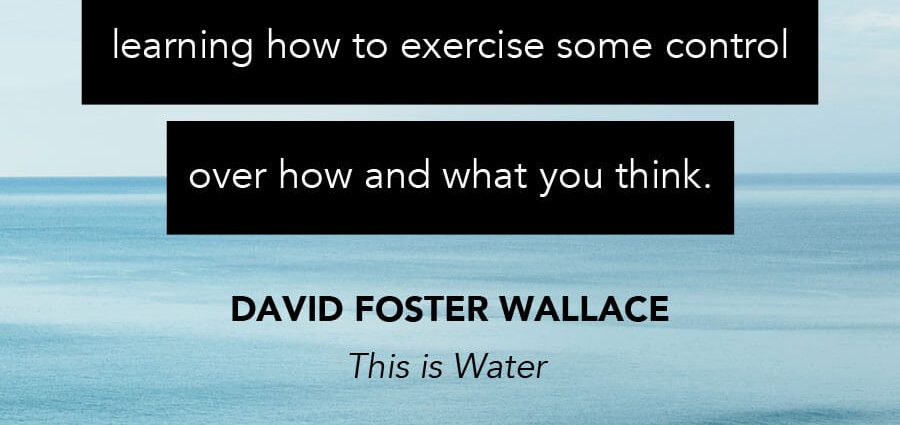鏡子、自拍、照片、自我探索……我們在反思或對自己的反思中尋找自己。 但這種搜索常常讓我們不滿意。 有些東西讓你無法客觀地看待自己……
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我們當中很少有人對自己完全滿意,尤其是對自己的外表。 幾乎每個人,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都想解決一些問題:變得更自信或更快樂,捲髮而不是直發,反之亦然,讓腿更長,肩膀更寬……我們經歷不完美,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尤其是在青年時期。 “我生性害羞,但對自己丑陋的信念進一步增加了我的害羞。 而且我相信,沒有什麼比外表對一個人的方向產生如此顯著的影響,不僅是外表本身,還有對它的吸引力或不吸引力的信念,”列夫托爾斯泰在自傳的第二部分描述了他的狀態三部曲“童年。 青春期。 青年”。
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痛苦的尖銳程度會減弱,但它們會完全離開我們嗎? 不太可能:否則,改善外觀的照片濾鏡不會那麼受歡迎。 整形手術也是如此。
我們看不到自己的本來面目,因此我們需要通過他人來斷言“我”。
我們總是主觀的
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客觀地認識自己? 當我們看到一個外部物體時,我們能從側面看到自己嗎? 似乎我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 然而,公正地看待自己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的感知被童年經歷的投射、情結和創傷所扭曲。 我們的《我》並不統一。
“自我永遠是另一個自我。 即使我將自己表現為“我”,我也永遠與自己分離,”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康在他的散文中說。1. ——與自己互動,我們不可避免地會經歷分裂。 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患有阿爾茨海默病的人在與自己進行對話時相信他正在面對另一個對話者的情況。 早在 XNUMX 世紀初,神經學家和心理學家保羅·索利爾就寫道,一些年輕女性在歇斯底里發作期間不再看到鏡子中的自己。 現在精神分析將此解釋為一種防禦機制——拒絕接觸現實。
我們習慣性的,或多或少穩定的自我認知是一種心理結構,是我們思想的組成部分。
一些神經紊亂會改變我們的意識,以至於病人懷疑自己的存在,或者他覺得自己像一個人質,被鎖在一個外星人的身體裡。
這種感知扭曲是疾病或重大衝擊的結果。 但我們習慣的或多或少穩定的自我認知也是一種心理結構,是我們思想的組成部分。 同樣的心理結構是鏡子中的反映。 這不是我們能感覺到的物理現象,而是有自己歷史的意識投射。
第一眼
我們的“真實”身體不是醫學所處理的生物的、客觀的身體,而是在第一批照顧我們的成年人的言論和觀點的影響下形成的觀念。
“在某些時候,嬰兒環顧四周。 首先——在他母親的臉上。 他看到她在看著他。 他讀懂了她對她的認識。 並得出結論,當他看時,他是可見的。 所以它存在,”兒童心理學家唐納德溫尼科特寫道。2. 因此,他者的目光轉向我們,是我們存在的基礎。 理想情況下,這是一個充滿愛意的外觀。 但實際上並非總是如此。
“看著我,媽媽常說:‘你去找你爸爸的親戚了’,我為此恨自己,因為爸爸離開了家。 五年級時,她剃了光頭,以免看到像他一樣的捲發,”34 歲的塔季揚娜說。
父母厭惡地看著自己的人可能會長時間認為自己是個怪胎。 或者也許急切地尋找反駁
為什麼父母總是對我們不友善? “這取決於他們自己的個性,”臨床心理學家 Giorgi Natsvlishvili 解釋道。 — 可以觀察到過度要求,例如,在一個偏執的父母告訴孩子:“小心,到處都很危險,每個人都想欺騙你……。 你的成績如何? 但是鄰居的孫女只帶了五個!
所以孩子有焦慮,懷疑他的智力和身體是否良好。 而自戀的父母,通常是母親,將孩子視為自己的延伸,因此孩子的任何錯誤都會引起她的憤怒或恐懼,因為這表明她自己並不完美,有人會注意到這一點。
父母厭惡地看著自己的人可能會長時間認為自己是個怪胎。 或者可能急切地尋找反駁,捆綁很多愛情故事以確保它們的吸引力,並在社交網絡上發布照片以收集喜歡。 Giorgi Natsvlishvili 繼續說:“我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尋求客戶的認可,這些都是 30 歲以下的年輕男女。” 但原因並不總是在家庭中。 有一種觀點認為,父母的苛刻是致命的,但實際上,這樣的故事可以在沒有他們參與的情況下出現。 相當苛刻的環境。»
這種嚴格性的指揮者既是大眾文化——想想超級英雄的動作電影和遊戲,以及模特極瘦的時尚雜誌——以及核心圈子、同學和朋友。
鏡像曲線
我們在鏡子裡看到的倒影和照片都不能被認為是客觀的現實,僅僅因為我們從某個角度看它們,這受到我們童年重要成年人的意見(包括不大聲表達)的影響,然後是朋友、老師、合作夥伴、影響和我們自己的理想。 但它們也是在社會和文化的影響下形成的,提供了榜樣,這些榜樣也會隨著時間而改變。 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完全獨立的自尊,“我”,沒有其他人的影響,是一個烏托邦。 佛教徒認為他們自己的“我”是一種幻覺,這並非巧合。
我們並不像我們猜測的那樣了解自己,在必要時收集信息,與他人比較,聽取評估。 即使在那些可以客觀衡量的參數中,我們有時也會犯錯誤,這並不奇怪。 臨近夏天,很明顯,許多女性穿著不合身的衣服,穿著涼鞋,手指伸出來……顯然,在鏡子裡,她們看到的是更苗條或更年輕的自己。 這是對現實的一種保護:大腦消除不愉快的時刻,保護心靈免受不適。
大腦對人格中不吸引人的方面也是如此:它在我們看來將它們抹平,我們不會注意到,例如,我們的粗魯、嚴厲、對我們周圍的人的反應感到驚訝,我們認為他們敏感或不可忍耐。
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在小說中這樣稱呼日記:“與自己的對話,與生活在每個人身上的真實、神聖的自我對話”
我們的自我形像也被我們想要獲得社會認可的願望所扭曲。 卡爾·榮格將這種社會面具稱為“角色”:我們對自己的“我”的要求視而不見,通過地位、收入水平、文憑、婚姻或孩子來進行自我決定。 萬一成功的表象倒塌,背後卻是一片空虛,一場嚴重的神經衝擊可能在等著我們。
通常在招待會上,心理學家會問同樣的問題:“你是什麼人?” 他一遍又一遍地要求我們用不同的綽號來描述自己,拒絕接受這種身份的社會角色:他希望我們不要習慣性地稱自己為“好辦公室工作人員”和“有愛心的父母”,而是試圖孤立我們關於我們自己,例如:«脾氣暴躁»,«善良»,«要求»。
個人日記也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 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在小說《復活》中這樣稱呼日記:“與自己的對話,與生活在每個人身上的真實、神聖的自我對話。”
觀眾的需求
我們對自己了解得越少,就越需要觀眾給我們反饋。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現代自畫像類型自拍如此受歡迎的原因。 在這種情況下,被拍照的人和被拍照的人是同一個人,所以我們試圖捕捉我們存在的真相……或者至少傳達我們對自己的看法。
但這也是對其他人的一個問題:“你同意我這樣嗎?”
試圖以有利的視角展示自己,我們似乎在請求允許將理想形象合法化。 即使我們在有趣的情況下捕捉自己,願望仍然是一樣的:找出我們是什麼樣的人。
技術的世界讓你多年來一直生活在觀眾認可的針尖上。 然而,理想化自己有那麼糟糕嗎?
雖然外部評估一點也不客觀,但畢竟其他人會受到不同的影響。 在江戶時代的日本版畫中,美女們在牙齒上塗上黑色顏料。 而如果倫勃朗筆下的達那厄穿著現代服飾,誰會欣賞她的美貌呢? 對一個人來說看起來很美的東西不一定會取悅另一個人。
但是通過收集很多贊,我們可以說服自己,至少有很多同時代的人喜歡我們。 23 歲的 Renata 承認:“我每天都會發布照片,有時會發布好幾次,並期待收到反饋。” “我需要這樣才能感覺到我還活著,並且有一些事情正在發生在我身上。”
技術的世界讓你多年來一直生活在觀眾認可的針尖上。 然而,理想化自己有那麼糟糕嗎? 許多研究表明,這樣做的人比那些試圖批評自己的人更快樂。
1 Jacques-Marie-Émile Lacan Essay Points (Le Seuil, 1975)。
2 “母親和家庭的鏡子的作用”,在唐納德 W. 溫尼科特的遊戲與現實中(普通人文研究所,201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