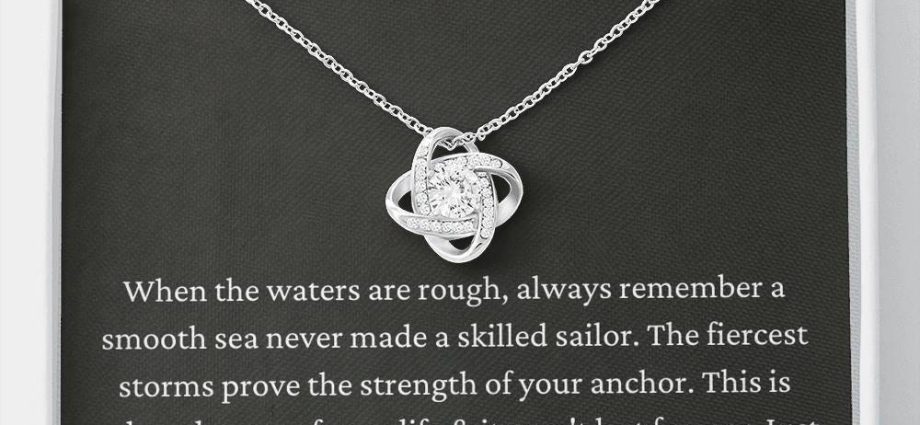內容
15 年 2019 月 XNUMX 日晚,社交媒體信息幾乎每分鐘都在記錄著火的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是法國的主要像徵之一。 許多人很難相信噩夢般的鏡頭的現實。 發生的悲劇不是大教堂歷史上的第一次,當然也不是歷史文化遺產的第一次損壞。 那麼為什麼我們會如此受傷和如此害怕呢?
臨床心理學家 Yulia Zakharova 說:“在當今充滿活力的世界中,手機型號在六個月後就過時了,人們越來越難以相互理解,我們正在失去一種穩定感和社區感。” “能被人們明確理解和分享的價值觀越來越少。
由作家、詩人、作曲家所唱的數百年和千年的文化和歷史古蹟,仍然是和諧與恆久的島嶼。 我們對巴黎圣母院的火災感到難過,不僅因為它是一座可能會丟失的美麗建築紀念碑,還因為對於我們個人主義者來說,成為更大事物的一部分,尋求並找到共同的價值觀仍然很重要. .
這就是他們對昨天在講俄語的互聯網上發生的悲劇的反應。
謝爾蓋·沃爾科夫,俄羅斯語言文學教師
“我們很少意識到永久性事物對我們的生活有多重要。 “這裡的一切都會比我長壽”不是關於失去的痛苦,而是關於它應該如何。 我們行走在世界大城市的永恆風景中,人們遠在我們之前就已經走到這裡,然後許多其他人消失了,並且這種情況將在未來繼續,這種感覺平衡並確保了我們的意識。 我們的年齡很短——這很正常。 “我看到一棵孤零零的橡樹,我想:森林的族長會在我被遺忘的時代倖存下來,就像他在父親的時代倖存下來一樣”——這也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閃電擊中我們眼前這棵巨大的橡樹並使其死亡,這是不正常的。 不是為了自然——為了我們。 因為在我們面前打開了我們自己死亡的深淵,它不再被任何東西所覆蓋。 橡樹的長歲證明比我們的要短——那麼從不同的尺度來看,我們的生活是什麼? 我們只是沿著地圖走,那裡一厘米有兩百米,在我們看來它充滿了意義和細節——突然我們一下子升到了一個高度,下面已經有一百公里了厘米。 在這張巨大的地毯上,我們生命的針腳在哪裡?
似乎在我們眼前,來自全人類度量衡室的參考儀表正在燃燒和融化。
當像聖母院這樣複雜而巨大的堡壘(對我們來說是一種可以理解和掌握的永恆形象)在幾小時內死去時,人們會感到難以形容的悲傷。 你記得親人的死亡,再次流下無用的眼淚。 巴黎圣母院的輪廓——當然不僅是它,而且它在某種程度上很特別——擋住了現在空虛的縫隙。 它張開得如此之大,以至於您無法將視線從它身上移開。 我們都去那裡,進入這個洞。 看起來我們還活著。 激情週在法國開始了。
好像很久沒有被覆蓋了。 似乎在我們眼前,來自全人類度量衡室的標準米,標準公斤,標準分鐘,正在燃燒和融化——理想狀態下,美的單位價值保持不變。 它堅持了很長一段時間,對我們來說堪比永恆,然後就停止了。 就在今天。 在我們眼前。 它似乎永遠。
鮑里斯·阿庫寧,作家
“在第一次震驚之後,這個可怕的事件最終給我留下了一些鼓舞人心的印象。 不幸並沒有將人們分開,而是將他們團結在一起——因此,它屬於那些使我們變得更強大的人。
首先,事實證明,這個級別的文化和歷史古蹟不是每個人都認為是國家的,而是普遍的價值。 我相信全世界都會為修復工作籌集資金,既漂亮又迅速。
遇到麻煩,不要復雜原始,而要簡單平庸
其次,Facebook 用戶的反應,極大地闡明了一個道理,即陷入困境的人不應該是複雜而原始的,而應該是簡單而平庸的。 同情,悲傷,不要聰明,注意不要有趣和炫耀,而是關於如何提供幫助。
對於那些在一切事物中尋找符號和符號的人(我自己就是),我建議將這個“信息”視為全球團結和地球文明力量的體現。”
塔季揚娜·拉扎列娃,主持人
“這只是某種恐怖。 我和我一樣哭。 從小,在學校裡,就有一個像徵。 總符號。 希望,未來,永恆,堡壘。 起初我不相信我會在某個時候看到它。 然後我反复看到它,愛上了我自己。 現在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淚。 主啊,我們都做了什麼?»
Cecile Pleasure,女演員
“我很少在這裡寫關於悲傷和悲傷的事情。 在這裡,我幾乎不記得人們離開這個世界,我離線哀悼他們。 但是我今天會寫,因為總的來說我完全不知所措。 我知道人們——他們死了。 寵物離開。 城市正在發生變化。 但我不認為這是關於像巴黎圣母院這樣的建築。 符號不亮? 他們是永遠的。 完全混亂。 今天了解了一種新的疼痛變體。”
加琳娜·尤澤福維奇,文學評論家
“在這樣的日子裡,你總是在想:但你可以去,然後,即使那樣你也可以,但你沒有去——該去哪裡急,永恆就在前面,如果不和我們在一起,那麼無論如何都要和他在一起。 我們會成功的。 上次我們和孩子們在巴黎時太懶了——聖禮拜堂、奧賽,但是,好吧,第一次就夠了,我們會從外面看到。 Carpe diem,quam minime credula 海報。 我想快速擁抱整個世界——同時完好無損。
迪娜·薩比托娃,作家
“法國人在哭。 事件震耳欲聾,一種不真實的感覺。 似乎我們都從某個地方是巴黎圣母院的事實出發。 我們中的許多人仍然只從照片中認識他。 可太可怕了,好像是個人的損失……怎麼會這樣……”
Mikhail Kozyrev,記者、音樂評論家、主持人
“悲哀。 只有悲傷。 我們會記住這一天,就像雙子塔倒塌的那一天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