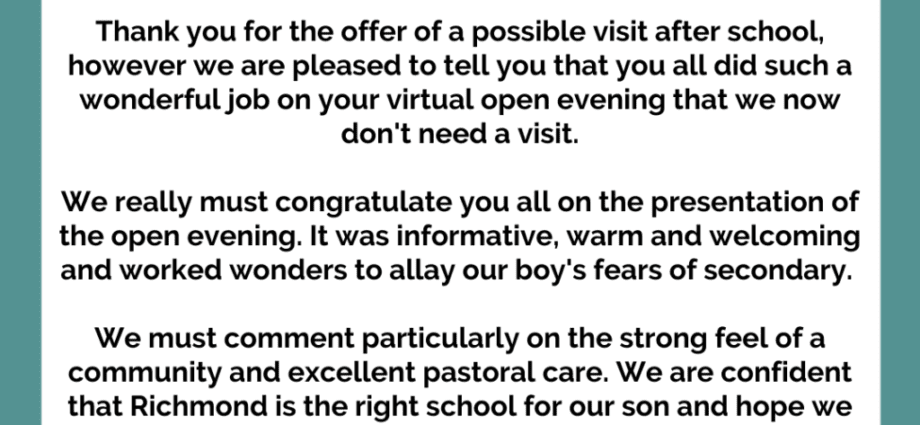“我女兒以為我們生來就是白人,長大後就變黑了……”
42 歲的 Maryam 和 10 歲的 Paloma 的證詞
我的堂兄去世後,我收養了帕洛瑪。 帕洛瑪那時才 3 歲多一點。 小時候,她以為你生來是白的,長大了就變黑了。 她確信她的皮膚以後會和我的一樣。 當我向她解釋事實並非如此時,她非常失望。 我告訴他關於異族通婚、我的父母、我們的家庭、他的歷史。 她非常理解。 有一天她告訴我 “我可能外表是白的,但我的內心是黑的。” 最近,她告訴我“重要的是內心深處的東西”. 勢不可擋!
和所有小女孩一樣,她想要自己沒有的東西。 Paloma 有一頭直發,夢想著有辮子、辮子、蓬鬆的頭髮“像一朵雲”,就像我有一段時間的黑人髮型一樣。 她覺得我的鼻子很漂亮。 從她說話的方式,從她的表情來看,她看起來很像我。 夏天,曬得全黑,我們把她當成混血兒,人們認為她是我的親生女兒並不少見!
我們在馬賽定居,在那裡我尋找一所適應其需要和悠久歷史的學校。 她在一所應用了 Freinet 教學法的多元化學校學習,學習適應每個孩子,課程由雙層組織,孩子們被賦予權力,按照自己的節奏相當獨立地學習。 . 它對應於我給他的教育,它使我與我個人討厭的學校和解。 一切都很順利,她和各行各業的孩子在一起。 但是我為她上大學做了一些準備,為她可能會提出的問題,為她可能能夠聽到的思考。
有很多關於種族主義的討論,關於膚色如何決定一個人將被如何對待. 我告訴她,作為一個黑人媽媽,也許我會被不同的看待。 我們談論一切,殖民主義、喬治·弗洛伊德、生態……對我來說,向他解釋一切很重要,沒有禁忌。 我在 Paloma 的經歷與我在白人母親身上的經歷大不相同。 她必須一直走到前線,為我辯護,面對種族主義思想。 今天,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帕洛瑪的皮膚更白,是不是因為我的六英尺和我的剃光頭強加了它,這值得尊重,如果是由於馬賽的多樣性,但它進行得很順利。 “
“與我小時候所經歷的相比,我覺得這對我的孩子來說更容易。 “
皮埃爾的證詞,37歲,利諾的父親,13歲,努瑪,10歲,麗塔,8歲
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人們總是認為我是被收養的。 總是有必要解釋我確實是我父親的兒子,因為他是白人。 當我們一起去購物時,我父親不得不通過指定我陪同他來證明我的存在。 人們在商店裡跟著我或斜視的情況並不少見。 當我們去巴西時,我母親來自那裡,我父親不得不再次證明我們的出身。 太累了。 我在一個相當富裕的環境中長大,並不是真正的混血兒。 我經常是學校裡唯一的黑人。 我聽到了很多相當邊緣的評論,中間夾雜著“哦,但是你,這不一樣”。 我是個例外,這些評論應該被視為一種恭維。 我經常開玩笑地說,我有時會覺得自己是個“假的”,黑體中的白人。
我的印像是我的孩子,三個小金發女郎不一樣!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採用的推定並不多。 人們可能會感到驚訝,他們可能會說“嘿,他們看起來不一樣”,但僅此而已。 當我們一起在人行道上的咖啡館裡,其中一個叫我爸爸時,我真的感覺到了好奇的目光。 但這反而讓我發笑。 我也玩它:我知道我的大兒子在學校被打擾了。 離開大學的一天,我去接他。 我的非洲裔、我的紋身、我的戒指,都有它的效果。 從那以後,孩子們就離開了他。 最近,當我去游泳池接他時,Lino 告訴我:“我確定他們會把你當成我的管家或司機”。 暗示:這些種族主義白痴。 我當時並沒有太大反應,他第一次跟我說這樣的話,讓我很驚訝。 他必須在學校或其他地方聽到一些事情,這可能會成為一個話題,一個他關心的問題。
我的另外兩個孩子確信他們是混血兒,就像我一樣,而他們是金發碧眼的,相當公平! 他們與巴西文化有著深厚的聯繫,他們想說葡萄牙語並花時間跳舞,尤其是我的女兒。 對他們來說,巴西就是狂歡節,音樂、舞蹈無時無刻不在。 他們並沒有完全錯……尤其是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看到我媽媽到處跳舞,甚至在廚房裡。 所以我試著把這種雙重遺產傳給他們,教他們葡萄牙語。 我們本應該今年夏天去巴西,但那裡的流行病已經過去了。 這次旅行保留在計劃中。 “
“我必須學習如何為我女兒的頭髮定型。 “
Frédérique 的證詞,46 歲,Fleur 的母親,13 歲。
我在倫敦生活了二十多年,芙蓉就在那裡出生。 她的父親是英國和蘇格蘭的混血兒,來自聖盧西亞,有加勒比血統。 所以我必須學習如何為我的小女孩的自然頭髮定型。 不容易 ! 一開始,我測試了產品來滋養和解開它們,這些產品並不總是很合適。 我向我的黑人朋友徵求意見,我還諮詢了附近的專賣店,以了解在這種頭髮上使用哪些產品。 我承認,我也不得不像許多父母一樣即興創作。 今天,她有她的習慣,她的產品,她自己做頭髮。
我們住在倫敦的一個地區,那裡有多種文化和宗教。 芙蓉的學校在社會和文化上都非常混雜。 我女兒最好的朋友是日本人、蘇格蘭人、加勒比人和英國人。 他們互相吃飯,發現彼此的特產。 我從來沒有感受到對我女兒的種族歧視。 這可能是由於城市的混合,我的社區或所做的努力,也在學校。 每年,在“黑人歷史月”之際,學生們從小學開始,學習奴隸制、黑人作家的作品和生活、歌曲。 今年,大英帝國和英國殖民都在節目中,一個讓我女兒反感的話題!
隨著“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芙蓉被這個消息所震撼。 她畫了圖來支持這場運動,她感到很擔心。 我們在家裡談論了很多,也和我的伙伴談論了很多,他非常參與這些問題。
在我們往返法國的旅行中,我目睹了對我女兒的種族主義思想,但幸運的是,這是軼事。 最近,芙蓉震驚地看到在一戶人家中有一尊黑色新郎的大型雕像,處於僕人模式,戴著白手套。 她問我家裡有這個是否正常。 不,不是真的,它總是讓我很生氣。 有人告訴我,這不一定是惡意的或種族主義的,這種類型的裝飾可能很流行。 這是一個我從來沒有覺得很有說服力的論點,但我還不敢正面接近這個主題。 說不定芙蓉會敢,以後……”
西多妮·西格里斯特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