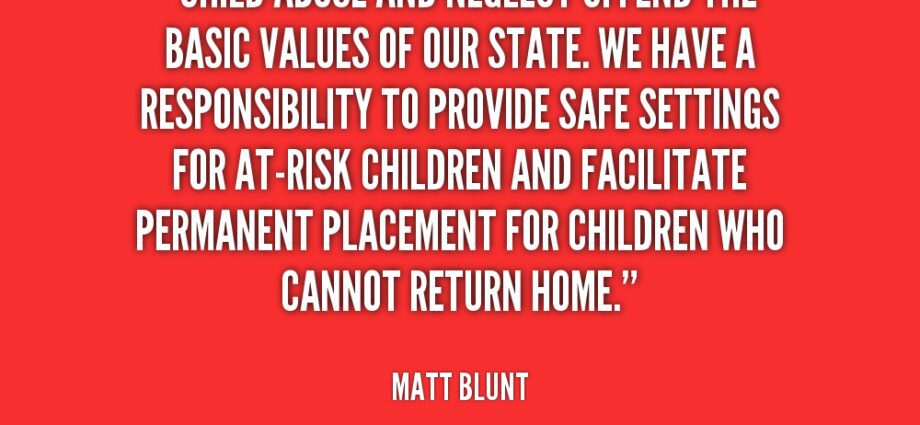父母遺棄問題、遺棄聲明和簡單收養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多年來一直以極強的立場引起激烈的爭論。
一方面:兒童保護的倡導者著眼於兒童與其家庭之間的聯繫的持久性,即使這意味著人為地保持這種聯繫並對兒童造成反復安置。
另一方面:早期發現父母遺棄和加速宣布遺棄的支持者,這將允許孩子獲得國家監護人的地位並被收養。 多米尼克貝爾蒂諾蒂顯然位於第二個斜坡上。 “我們有家族傳統。 對於我們知道不會回家的孩子,我們是否應該考慮其他系統? 促進收養程序? ”
兒童保護法,永恆重啟
她不是第一個關注這個問題的部長,她不是第一個想給那些應該在 ASE 的接待結構中“萎靡不振”的孩子一個“第二個家庭機會”的部長。 在她那個時代,納丁·莫拉諾 (Nadine Morano) 提出了一項關於收養的法案(從未提交投票,但遭到強烈批評),其中一個組成部分指出:“兒童社會援助 (ASE) 必須每年評估,從第一年開始安置,如果孩子的親生家庭遺棄了孩子:然後檢察官辦公室可以要求進一步調查或直接向高等法院提出放棄聲明的請求,這將使其完全可以被收養”。 昨天,在南特,多米尼克·貝爾蒂諾蒂(Dominique Bertinotti)與負責民政事務的副檢察官面對面。 這是他所提倡的:” 當安置似乎被延長而不詢問兒童的最大利益問題時,允許控方出庭是相關的。 “。
正如我們所見,保護兒童和貫穿其歷史的意識形態鬥爭超越了政治分歧。 右翼部長 Philippe Bas 在 2007 年通過了一項改革兒童保護的法律,並將生物學聯繫置於 ASE 使命的核心位置,但她也是右翼部長 Nadine Morano,她希望以加快放棄程序並將光標移到家庭紐帶的較早中斷處。 一位左翼部長現在正在接過火炬。 使用這種尺寸的陰影: 多米尼克貝爾蒂諾蒂希望採用簡單的收養方式,這樣就可以為孩子提供一個新家,而不會消除他與親生父母的親子關係。
沒有定義或參考的放棄
在這個問題上,很難區分現實立場和意識形態立場。 許多社會工作者欣然承認,我們從一開始就知道他們永遠不會回家的兒童很早就被安置,然而,這並不是遺棄程序和持續時間的穩定項目的對象。 “絕對有必要提前一天在部門裡查明六個月沒見父母的孩子,迫切需要一個關於忽視概念的參考框架,評估技術將使團隊從他們的陳述中解脫出來”,Meurthe 和 Moselle 總委員會的 Anne Roussé 提出,她與其他人一起發起了一項請求供國家收養。 就我而言,我的印像是,面對許多孩子的長期安置和不穩定的道路,社會工作者的關注和質疑往往會增加。 今天的專業人士似乎更快地譴責一種有些教條的傾向,即想要保持一種本身已經變得有害的聯繫。 但這只是印象。
數字,偉大的法國藝術模糊
“家庭主義”事業的積極分子,無論如何認為ASE的主要作用是讓孩子接受他的親生父母教育的人,仍然非常活躍。 然而,最著名的“家庭紐帶”先驅之一,博比尼兒童法庭院長讓-皮埃爾·羅森維格本人負責監督家庭法案的一個工作組。 我們認為與部長的討論一定很活躍。 讓-皮埃爾·羅森維格 (Jean-Pierre Rosencveig) 一直肯定,真正被父母遺棄的孩子很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足以明智地提及功能障礙),因此收養只能構成“一個非常小的兒童保護工具”。 因此,在做出決定時,必須了解被安置的未成年人中被遺棄兒童的確切數量。 該部的服務讓人想起 15.000 名兒童,這實際上是審查我們的兒童保護系統的理由。 但由於缺乏精確的定義和可靠的統計工具,它只能是一種估計,因此很容易受到家庭紐帶的支持者的質疑和質疑。 這種藝術上的模糊性不利於試圖定義問題的外部觀察者的任務,例如記者。 因為相信誰? 在這場反復出現的複雜辯論中,我們可以將最大的合法性歸於誰? 當從一個專家到另一個專家,從該領域的一個專家到另一個專家,答案截然相反時,我們如何才能盡可能接近實踐和經驗的現實?
這就是為什麼我被引導轉播的許多主題缺乏可靠的統計數據已成為我目前的小迷戀。